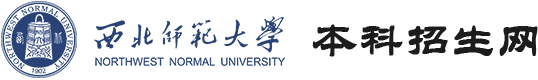理想不息,浪漫不止
小忆我和“我们”的时光
“离开师大数十年,但一半的梦与师大有关”我校校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家魏明孔先生的这句话经常让我无限感慨。我自2002年从师大硕士毕业,至今也不过十个年头,当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甚至更多的梦与师大有关。或言对我而言,当有百分之五十的梦与“我们”有关,这也并不为过,因为在本科四年的时光中,我在大学的活动轨迹有一半以上与“我们”相濡以沫、不分彼此。
只是确已似乎好久已未曾梦见那一本本深蓝底色、印着鲁迅木刻头像、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我们》了。
难道忘记了?不,不是,不是忘记了,是已铸就在了自己的那一段生命中,和“我们”相融的过于彻底,未留下丝毫的空间,没有想的余地,没有梦的余地,没有悔的余地,没有恨的余地,惟有那一段与“我们”相融为一的生命历程,横亘在已走过的岁月中,任凭日晒雨淋、风吹雨打。
只有那些细节就像雨后带露的鲜红的果实,被我深深地窑藏了起来,点点滴滴,任凭世事沧桑,皆是原汁原味,且岁月愈久,其色其味愈浓烈绵长。
惟一一份以报纸形式出现的《我们》
大概是在九六年的春天,也就是我进入西北师大第二学期的时候,我从已要毕业的学兄何满意那儿接过诗歌学会会长担子,在校报主编、诗歌学会前任会长徐兆寿老师的支持和指导下开始了“我们”新的旅程,在此之前,《我们》已有一两年没有出过新刊。好像是马克,在已消失了的盘旋路边,无比失落地说:“在西北师大,只剩下我和何满两个写诗的人了......”
第十八期《我们》便在这年的春天里孕育着,我,李雁彬,杨恒,好像还有马俊春和王峰,我们骑着自行车,沿着北滨河路一路向东,一直到段家滩的兰州商学院,在商学院的学生宿命,和擅长美术设计的张隆、蒋引一起,进行文章的排版、剪贴和插画,由于缺少经验和人手,我们且又急于把《我们》的旗帜重新树立起来,这一期的《我们》是以报纸的形式出现的,这也是《我们》历史上惟一一份以报纸的形式存在的会刊。为了节省费用,我们先把文章根据事先设计好的样式在A4的纸上打印出来,再一篇一篇剪贴到四张8开大的纸上,剪贴完成后,再到油印机上印制,印制成两份8开大的报纸,报纸的原样虽然层层叠叠满是补丁,但印出来的报纸却也干净、漂亮,带着油墨的清香。
因为有了诗歌,满是年轻人的校园开始沸腾了,诗歌再一次唱响了我们心中埋藏的浪漫与梦想。
扛起鲁迅的大旗,我们勇于担当
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社会再一次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到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的车轮已是开足了马力呼啸奔驰在国际社会的舞台上,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北京,中国正在以世界工厂的角色为全球日夜不停地生产着各种生活、生产用品,中国的主流社会正在把“中国制造”推向全球。在北京,在广州,在所有经济浪潮波涛汹涌的地方,诗歌的桂冠不再为年青人青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北岛、舒婷等为代表的诗人们开创的诗歌盛世似乎已一去不返,那时的年青人,有了更加开阔的挥洒青春、追逐梦想的经济大舞台,下海、经商、创业,用实业和财富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包括许多文人在内的中国人的选择。
西北师大所在的甘肃兰州自然也受到这一大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但毕竟那时电脑才刚刚走进人们的工作,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尚未普及,兰州依沿袭着内陆城市的宁静、恬淡与矜持,诗歌的种子、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为诗歌而燃烧青春的梦想得到了保护和传承。多年以后我想,经济欠发达,信息闭塞,思想保守,这既是甘肃的不利因素,也正是甘肃在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中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原因所在。坚持下去,唱出自己的最强音,让甘肃成为物欲横流的大世界中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家园,让西北师大成为诗歌的发祥地和孕育地,让兰州成为诗人们向的地方!我们便在那时这样做了。
在徐兆寿老师和叶知秋先生的指导下,我们举起了鲁迅的旗帜,提出诗歌要有社会责任感,诗作为社会的灵魂,不可以颓废,不可以自轻,诗人要继承中国传统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命意识并在新的时代里将这一使命发扬光大。在一九九六年的秋天,我们推出了西北师大诗歌协会的第十九期会刊《我们》,这一期《我们》恢复了原来16开本的模样,正文70余页,除了在校学生的作品,《我们》在内容上也得到了徐兆寿、彭金山、王珂等在校老师的亲身参与与支持,我们还约到了高平、何来、叶舟、扎西才让、颜峻等这些在诗坛上声名远扬的往届诗歌学会会友的大量优秀诗作,这一期的内容丰富、厚重,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颇有代表性的一份民间文学刊物。
在第二年的春天,我和徐兆寿老师带着这份刊物到了北京,拜访了丛维熙、邵燕祥、谢冕等文坛星宿;我们到《诗刊》编辑部,拜访叶延滨、邹静之、雷霆等诗人;我们还到北师大、北大,与他们的文学社团交流......北京那年春天的风沙似乎很大,但却丝毫无碍我们怀着满腔的热情到处宣扬《我们》、宣传《我们》的诗歌和精神。
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中,诗歌是每个人心灵深处流淌的河,只要有生活,这隐藏的河就会发出声响,《我们》便是这样,在全国商业化的浪潮里独自奏响了心灵的绝唱。不仅仅是在西北师大,不仅仅是在兰州,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很快重新成为各地诗人们谈论的热点,一些从未有任何联系的诗人也主动给我们写信、投稿,部分北京高校的文学社团纷起行动,积极应和《我们》的诗歌精神与文学主张。
这一期的《我们》封面底色是凝重的深蓝色,左上角有墨印的鲁迅木刻头像,此后的几年里,鲁迅的木刻头像成为《我们》的标志性图像,这一期以来形成的办刊风格也一直得以延续。
也是从这一期开始,西北师大诗歌协会改组为西北师大文学联合会,我这个诗歌学会会长也就成为首任文学联合会会长。虽然名称变了,但文学的传承没有变,我们更加包容,我们的队伍更加壮大,《我们》成为包括诗歌、散文、文学评论、思想讨论等多种文学形式在内的精神盛宴。
我们在一起
师大有着良好的诗歌传统,单就诗歌学会而言,自从第一任会长彭金山先生算起,到我作为第十任会长,已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从《我们》走出去的诗人不计其数,从我们走出去的诗歌爱好者们不计其数,“我们”不分系别,不分届次,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一提起《我们》,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感情。
那是无数代师大人放飞青春的梦想的地方。
在我担任学会会长的三年时间里,“我们”中走出的诗人与作家现在尚不能定论,但那时出版的会刊是历任会长中比较多的,组织的各类文学沙龙及文学活动也颇有声色,尤其是九七年在师大的大礼堂组织的“诗歌音乐会”,堪称为甘肃文坛上的一件盛事。那时,兄弟院校的各文学社团经常到师大参加文学活动,兰州医学院的《火鸟》文学社、西北民院《五色石》文学社、兰州大学《五泉》文学社、兰州电力学校《太阳雪》文学社、甘肃教育学院《涛声》文学社......都是师大文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与响应者。“我们”甚至在九八年左右还召开了兰州高校文学联合会的筹备工作,这一计划后来因为审批程序过于复杂等原因搁浅,但并影响如火如荼进行的各类实际活动。在那时,“我们”不仅是师大文学青年的精神家园,也是兰州各高校文学社团间各类文学活动的组织者、推动者。
这一切的背后,除了作为当时师大学生的我们全身心的投入以外,还有众多作为师大老师的“我们”、作为师大领导的“我们”、作为师大校友的“我们”,他们不分系别,不论届次,他们也作为“我们”的一部分,为“我们”的成长倾注爱、倾注心血,倾注支持和理解,更为“我们”当中这些学生的成长倾注爱、倾注心血,倾注支持和理解。
多年以来,我一直心怀感激,今天,恰值母校110年校庆,“我们”要出《我们的文脉》一书,我方能在这,为那些始终心系“我们”、无私为“我们”的薪火相传默默耕耘的人们表达我的敬意!因为这里有我们要找的真正的文脉!
徐兆寿老师那时是校报编辑部的主编,作为诗歌学会经曾的会长,他把振兴、发扬我们的工作当成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在那一段岁月里,除了工作和创作,他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在了“我们”的事业中。长长的梳得整齐而光亮的背头、鲜艳夺目的红色领结是他那时颇具诗人气质的标志性的形象,他狭小的单身宿舍几乎成为学会开会、组织活动的办公场所,为了给《我们》找到便宜、甚至不收费的印刷厂,我们从培黎广场坐上公交车,一路摇摇晃晃,倒上几次车,一直到兰州医学院,去求助他的同学。。。。。。似乎是在秋天,在兰州医学院校园的深处,我们找到一幢五六十年代建筑的大平房,岁月久远,他那位同学的大名已忘记了,只记得在那找到了要找的人,说了好些的话,但并未得到期望的支持和理解。为了宣传和推动《我们》,九七年的春天,徐老师带着我到北京游学,《我们》因此再一次为全国的诗坛所了解,也鼓舞了众中的诗歌中人。但这一行程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那时我记得他惟一的财产,就是一台内存为4兆或8兆的台式电脑......这次的活动,仍是由他牵头组织,我倍加感慨,无论何时,他对“我们”仍情笃如初!
彭金山老师那时是中文系的教授,他是诗歌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是《我们》的缔造者,也是我们中倍受尊重的长者,但凡学会的活动,他都不遗余力,记得有一回组织一个文学讲座,他带着我,亲自到市里去请省作家协会的何来主席,我至今记得,去的那个地方叫平沙落雁。这个地方具体在兰州的那个位置我到现在也不太清楚,只是这个岁月的片段、这个地名颇具诗意,叫人难忘。
还有中文系的叶知秋、邵宁宁等诸位老师,他们不计酬劳,只要是学会的各种活动,只要去邀请,他们没有任何教授的架子,都能准时出席活动且予以指导。
我们的活动在当时也得到了学校领导们的支持,无论当时的校领导王福成书记、赵金保校长,还是现在的校领导刘基书记,都欣然担纲了《我们》的顾问,遇到学会的重大活动,他们竟能在百忙之中拨冗参加,且常有具体的指导意见。还记得那时有位相熟的从事行政工作的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院系里重大活动校领导不一定参加,你们的活动校领导肯定参加!意思是学院的活动院长请校领导,校领导不一定参加,而我们这个学生社团组织却一请一个准。当时,给我们担任顾问的还有李志正副校长、校党委宣传部长张俊宗老师、中文系赵逵夫先生、彭金山老师,还有省作协主席高平先生、何来等诸位老师、先生。有了他们的指导和支持,我们便有了更加丰沃的土壤,更加广阔的用诗歌书写青春的舞台。
在我担任会长的几年里,黄泽元老师是学会的名誉会长,吕文英老师是责任编辑,徐兆寿老师简直就是《我们》专职的指导老师,彭金山、张俊宗、叶知秋、李迎新等老师也经常做一些指导工作。
在那些年里,我们也得到了校友们的无私支持与帮助,张子选、叶舟、王安民、颜峻、张海龙、扎西才让、敏彦文,这些我们历届学会的学兄、会友们,也经常用各自的方式给我们以大量的支持与帮助。
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学正如“铁打的营盘”,而学生便是那“流水的兵”,《我们》虽然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社团,但新生一届届地来,老生一届届地走,给一届届的学生撒播文学的种子的,便是这西北师大这座“铁打的营盘”,是这座古老的大学里生生不息传承着文学与理想的守夜人,是怀着理想与爱心辛勤耕耘着、浇灌着的师长们!是人在天涯,心系我们的亲历者们,在这里,大家共同呵护着我们的家园,让我们的文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那些难以忘记的老朋友
在我担任会长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由诗歌学会到文学联合会,直到我大学毕业,总共编辑出版过五期《我们》。在这期间,有无数的同学们,包括师大本校的、兄弟院校的,他们常常利用课余及自己的休息时间,为我们的出版抄抄写写,为我们的活动跑前跑后,如今,老朋友们已被岁月的风吹散在了时代的各个地方,但眸然回首相望,核桃树下诗声良朗朗,烛光依旧摇曳......,大礼堂里,各种装扮的诗歌精灵栩栩如生......岁月漫漫,如四季的轮回,如城市的变化,如地位的升降,如皱纹渐上心头,但有一段历程,虽在天涯,却似比邻。
这次索木东电话约稿,让我两个晚上失眠,那么多的人和事,如何几行文字理得清,但我还是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快把这篇稿子写出来,然后再把他窑藏起来,免得我今晚又思绪横飞难以收拢。
《我们》第十八期,1996年春出版,主编是万小雪;编辑有李雁彬,杨恒,马俊春、柴春芽、王峰等同学。
《我们》第十九期,1996年11月出版,主编是方孝坤和李雁彬,编辑人员有张文静、李胜会、王峰、杨晓龙、卢雄、裴亚宏、习一帆、雷涛、苏清华、于琛、冯舒翔、王鹏程等同学。
《我们》第二十期,1997年的10月出版。主编是李雁彬和我兼任,编辑人员有索木东、王峰、杨晓龙、习一帆、阎海东、张义洁、李晓荣、赵鹏、李虎林、李晶等同学。这一期的美编是张雅宁。
《我们》第二十一期,1998年4出版。主编是习一帆,编辑人员有索木东、王峰、马超、汪磊、赵晓辉、冯钰、阎海东、陈玲昌、李晓荣、雷涛、吴莉、秦雅、何金玉、阿雨、刘高峰等同学;
《我们》第二十二期,1998年十二月出版,此时我读大四,正在考研,已辞去了会长的职务。当时,低年级的秦雅、王强、马超、赵晓辉、冯钰、陈玲昌、刘国华、孙裕平、刘雪琪、马宝林、马红霞、赵凤英已成长为文学联合会的主力,我和方孝坤、索木东、杨恒、引桥春芽、李虎林组成了文学联合会的理事,形成了新老有序交替的良好格局。秦雅是那一阶段的代理会长,习一帆和王峰负责主编了我们这一届学生在校时的最后一期《我们》。
除了这些直接参与了《我们》的活动组织或编辑工作的,还有如周潇隆、王宏、姚成福、姚小淑、苏旺辉、王文阳、莫尊理、张雅宁、殷志华、张巍、何苇鸿、齐彦平等好专多朋友们,他们一起用诗,用青春纯洁而富有激情的歌,汇成了难忘的我们!
时光可以流逝,容颜可以沧桑,社会角色可以各异,但十里店一带黄河的涛声为证,那些岁月我们携手同共亲历,勿相忘记!
(注:本文收录于2012年出版的《我与西北师大》)